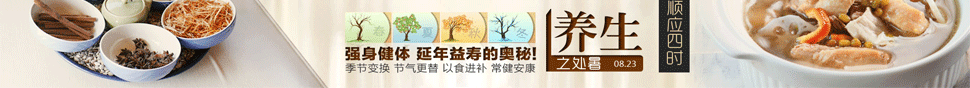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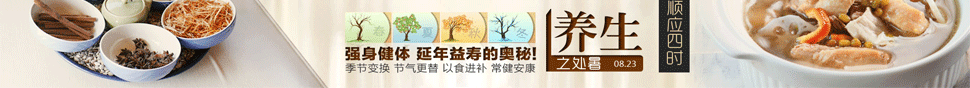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这个“世界法院”由15位法官主持,他们全都来自不同的国家,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选举产生。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二条,“法院以独立法官若干人组织之。此项法官应不论国籍,就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中选举之。”到目前为止共有七位中国籍国际法院法官(包括两位中国籍常设国际法院法官)
王宠惠:-年任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的前身)法官,曾任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北洋政府司法部长。
郑天锡:-年任常设国际法院法官,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
徐谟:-年任国际法院法官,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
顾维钧:-年任国际法院法官,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
倪征燠:-年任国际法院法官,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
史久镛:年2月6日,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年2月至年2月任国际法院副院长;年2月6日当选国际法院院长。
薛捍勤:年6月29日当选国际法院法官至今。
◎宗道一/本文发表于年
引子
据新华社联合国(年)11月10日电,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于当天选出国际法院的5名法官,他们是从17名候选人中选出的。中国的史久镛当选。同一天,《人民日报》记者何洪泽自联合国报道,史久镛在第一轮投票时即以多数票当选。报道称,史久镛今年67岁,是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弹指九载寒暑过去。年10月21日,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史久镛先生再次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他是57年来,第3位连任的中国籍国际大法官。年2月8日,77岁的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副院长。3年后,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这是自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此项重要职务的中国人。
年初秋,当倪征日奥在海牙和平宫收拾行囊,准备结束最后一段任期的时候,中国另一位资深法律专家史久镛先生被推荐提名为国际法院法官的候选人。虽然正式选举将于当年初冬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但他的当选已成定局……是年仲夏,笔者在北京已风闻史久镛教授将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的竞选,即乘隙在其寓所与这位浙江宁波籍的外交部资深国际法专家作了数小时的访谈……
1、史久镛生在浙江宁波,从小随父母来到黄浦江边。满街飘扬的太阳旗和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使他萌发了最初的爱国主义幼芽。他和朱启祯等中国外交界资深人士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年10月9日生于浙江的史久镛教授,在三四岁时便随大人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民国小学结束了最初的正规教育后进入了在上海滩久负盛名的雷士德中学。这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坐落的英租界,教师全部用英语上课。史久镛那一口纯熟的英语就是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年,英国人自然不会料到,这所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学校竟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钱嘉东(前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裁军事务大使、国际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长),前驻美国休斯敦、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汤兴伯是比史久镛高几级的同学。李道豫(前外交部部长助理、国际司司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则比史久镛低几班。而前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梁于藩还是史久镛的同班同学。
虽然敌伪“孤岛”时期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呻吟挣扎,但相对而言,外国租界尚残留几分“祥和”气氛。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迅速和英国人交上了火,英租界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天下。当时,史久镛一家住在虹口英租界,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白渡桥。他无可奈何地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这使得少年史久镛有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过外白渡桥,对史久镛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亡国奴的生活常常令史久镛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史久镛经常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里。当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倚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父母关切的目光时,史久镛的心里总是升腾起无限的惆怅。爱国主义的幼芽,抗日进步思想的苗子,渐渐在史久镛年轻的心中萌生、滋长……
年夏,史久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和北平的燕京大学一样,圣约翰大学也是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长长的名单可以排出一大串:前驻丹麦兼冰岛大使陈鲁直、成幼殊夫妇,前驻瑞士大使田进,前驻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大使顾家骥,前驻土耳其、埃及大使詹世亮,前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黄嘉华、前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纪立德、前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胡洪范,以及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即使就政治系而言,史久镛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后来涉身新中国外交界,如八届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朱启祯,还有汤兴伯、胡洪范等,都是史久镛的同窗好友。
但是,尽管朱启祯、胡洪范、汤兴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健将,甚至史久镛还和朱启祯在同一个教室听过《各国政府政治体制》的课,过从甚密,史久镛还是钻进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小天地。由于家庭的影响,也由于抗战胜利,史久镛开始渐渐远离政治社会。那个时候,史久镛信奉的是“读书救国”。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偏偏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于年来到大洋彼岸,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公法系深造。
2、目睹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和黑暗,他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朦胧的革命思想。从电视荧屏里看到了新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在美国本土怒斥奥斯汀。他惊讶,他振奋,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朴素好感驱使他毅然中断自己的学业和研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像史久镛这样家境富裕的学生也会加入“打工仔”的行列。家里带去的钱用完了,而新中国的成立又导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尖锐对峙的局面,父母无法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汇钱。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维持学业,史久镛也成了“打工一族”。不过,他比一般“打工仔”的景况要好得多。
史久镛在父亲熟识的一家美国公司里当“计时工”。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化验室里配染料,活儿还算轻松。即使是这样,没有学过《资本论》的史久镛还是多少“窥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某些“秘密”。年夏,半工半读的史久镛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国际法硕士学位。
近3年的异国学子生涯,他多次目睹了和旧中国如出一辙的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老板可以任意开除工人。每年圣诞节火树银花的夜晚,通宵达旦歌舞升平的氛围,慈祥可爱的圣诞老人,这一切和流落街头瑟瑟发抖的乞丐、流浪汉形成鲜明的对比。给史久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一系列认真的思索。但是,在史久镛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的却是几个月后。那时,他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母校从事国际法研究,攻读博士学位。
年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一架载着新中国的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在纽约机场徐徐降落。中国政府的大使衔特派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将军(后任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偕其顾问乔冠华(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新中国外交官踏上美国大地。4天后的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讨论中国政府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开始后,伍修权即作了长篇演说。这是伍修权等人带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与希望来到联合国后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次发言。他愤怒地控拆了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罪行。嗓门很高、劲头特足的伍修权把灾难深重、饱尝酸辛的中国人民憋了一百多年的怨气、怒气一下子全部倾泻出来:“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 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的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伍修权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现在正走的是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年究竟不是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伍修权的发言震撼了联合国,震撼了美国,也震撼了全世界!
当时,11个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和应邀与会的各国主要代表围坐在会议大厅的马蹄形长桌前,蒋帮“代表”蒋廷黻与伍修权相对而坐,美国代表奥斯汀就坐在伍修权旁边。在与平日判若两人的伍修权满腔义愤、慷慨陈词,挥手怒斥美国侵略罪行的时候,耷拉着脑袋的蒋廷黻用手遮着前额,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沮丧相。而奥斯汀则一脸尴尬,歪着嘴角似听非听,一半恼怒,一半无奈。很多旅美中国人,如美国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教授吴仲华博士,国民党前驻伊朗、泰国大使李铁铮教授等在旁听席上耳闻目睹了这令人拍手称快、激动人心的精彩场面。史久镛是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这令一百多年来、饱尝屈辱与苦难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难忘的一幕,史久镛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他的胸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敌伪时期的“孤岛”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标牌,连同凶恶的宪兵,狂吠的狼犬,像叠印般地在脑海里出现,真是心酸往事历历,低回不堪回首啊!而如今,伍修权就这样在美国本土,几乎是指着奥斯汀的鼻子,面对面地予以讨伐,痛斥,而奥斯汀只能硬着头皮听着。这世道真的变了!伍修权将军历时两个小时,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控诉,真是一篇畅酣的檄文!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旧中国近百年来的“叩头外交”总算划上了句号,一去不复返了!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史久镛的心底第一次涌动着那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感!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史久镛开始有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
很快地,朝鲜战场捷报频传,中国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让克拉克无可奈何地坐到开城板门店停战谈判桌前签订了停战协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啊!”史久镛在心里默默地想。他的心里再一次涌起了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这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里,史久镛再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埋首书案。“青春作伴好还乡”,史久镛还没有来得及戴博士帽,便和吴仲华博士等学者、科学家差不多同时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平心而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人心的谣言,什么“马思聪被枪毙了!”等等,踏上归途的史久镛当时似信非信,还真有点不踏实。但是,凭着一股炎黄子孙固有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史久镛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3、在金陵古都,石头城下,他虽然一度登上中学教坛,讲授“西洋历史”,但是最终成为中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他一生与国际法结下不解之缘。不过,从80年代开始,他的舞台移到了纽约、日内瓦、香港……
年1月,回国不久的史久镛由高教部分配到南京师范学校讲授“西洋历史”。国际公法硕士成了中学历史教员,个中情由在那个时代是众所周知的。肃反运动,批俞平伯、反胡风……,在那些年月里,即使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遑论是史久镛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瓜田李下,受人猜疑。史久镛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虽然他亦曾困惑,亦曾彷徨。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是春风雨露,是和煦阳光,中国的知识分子苏醒了!久旱的禾苗又逢甘霖,史久镛的境况很快就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史久镛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史久镛就这样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刚出头的史久镛又入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史久镛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间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以外,他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又到国际法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国际法的研究,这给步入晚年的史久镛带来一个大显身手的极好机会。史久镛无限欢欣,豪情满怀,他生命旅程中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了!
年春,史久镛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紧接着,他又作为中国财政部访问世界银行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再度来到纽约。从此史久镛和联合国结下不解之缘。从年起一直到年,史久镛以顾问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四度来到联合国,参加第六委员会的工作。
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即法律委员会,负责大会期间有关法律问题的审议,其议题主要包括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和一些根据联大决议就某些专题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如宪章特委会、不使用武力特委会、反对雇佣军公约起草委员会、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法律议题,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外交使团和代表的保护和安理会等。随着中国国内法制建设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国际法律工作日益重视,进一步加强参与,先后参加了宪章特委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作为最早参加第六委员会的新中国代表之一,史久镛比较全面和积极地参与了该委员会的工作。从年开始,一直到年,史久镛先后连续四年出席第35、36、37、38届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代表。
史久镛在联合国崭露头角,进一步施展影响的是他当选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之后。年依据联大决议建立的联合国国际委员会是联合国的一个带有立法性质的主要法律机构,其宗旨是“促进国际法之逐渐发展及编纂”。国际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就一些国际法专题起草条文草案并将其提交联合国大会,有时也应联大的请求就特定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大会提出报告。该委员会的工作兼及国际司法范围内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着重于国际公法方面。国际法委员会由34名经联合国各会员国提名、由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当选委员必须“在国际法方面有公认的能力”,委员会的组成应能“代表全世界的各主要文明和法律体系”(实际上,从历史上看,西方法律的传统观点在国际法委员会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委员会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工作,不代表本国政府,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自前文所述的中国国际法专家倪征教授于年首次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后,中国广泛地参与了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年11月倪征教授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后,现任外交部法律顾问黄嘉华于年获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国际法委员会改选中,中国候选人史久镛以亚洲地区最高票当选为委员。年11月国际法委员会改选时,史久镛再度当选。他是这个委员会唯一的一位连选连任的中国籍委员。7年来,史久镛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克尽职守,卓有成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39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走马上任不久的史久镛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起草委员会委员。在次年5月初到7月举行的第40届会议上,史久镛参与了“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简称“危险责任”)、“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简称“水道”)、“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治案”(简称“治罪法”)“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简称“信使地位”)等所有专题的审议,并担任该届会议的报告员。这是自中国进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以来,中国籍委员首次参与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在本届会议上,史久镛对“危险责任”、“水道”、“治罪法”、“信使地位”诸专题发表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特别是他对“治罪法”专题所作的发言还受到特别报告员的重视。两年后,史久镛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42届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90年代开始后,史久镛还先后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第45届联合国大会,亚非国家法律协商委员会第30届会议(开罗)等重要国际会议。作为联合国环境署的中国专家,史久镛年参加了在日内瓦、内罗毕举行的关于审议蒙得维的亚计划高级专家会议。年7月,史久镛当选为环境法国际理事会成员。在此前后,史久镛多次以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不过,令史久镛终身难以忘怀的还是年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那时候开始的七、八年间,史久镛一直是谈判工作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法律顾问,在旷日持久、并不轻松的谈判中,史久镛参与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3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的起草工作。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几乎所有的中国政府的首脑人物都参加了这一盛会: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吴学谦、姬鹏飞、鲁平……。史久镛就站那位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脱颖而出的女译员张幼云(前驻英国大使馆政务参赞,劳动部国际司司长,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特别顾问)的后面,而张幼云的前面就是“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在这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动了感情,她对张幼云也像是对大家说:“我们看到了历史是如何写成的。”引以为豪的是,史久镛也是这光辉的历史篇章的书写者。
两年后,史久镛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纽约一间普通房间里的电视荧屏上第一次认识了伍修权将军等真正的共产党人起,到年差不多是整整36年。如今,他早已成为了这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一员。真是沧海桑田,令人感慨万端,尽在不言之中。
史久镛教授在海牙国际法院的任期从年2月6日开始,任职9年,真可谓任重道远。当年史教授踏上履新征途之际,正是英姿勃勃的祖国飞雪迎春之际。
年2月8日,国际法院选出新一任院长、副院长。来自法国的纪尧姆当选为院长,史久镛当选为副院长。
弹指九载寒暑过去,史大法官果然为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第一个9年任期届满前夕,那是年的深秋时光,史久镛的故国正是天高云淡、枫叶如丹。
10月21日,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史久镛先生和来自日本、德国、斯洛伐克、塞拉利昂的4位资深望重的法学家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人们注意到:史先生与塞拉利昂的克罗马一起连任!他是57年来,第3位连任的中国籍的国际大法官。
年2月6日,是史久镛先生再一次走马上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任期3年,可以连选联任。这是自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的58年间,第一位担任此项重要职务的中国人。
让我们衷心地为年届耄耋的史久镛大法官祝福,愿他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愿史先生在新世纪里为世界再立勋绩!
*******
文章推荐(在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engdeweideyaa.com/mdwdydc/5206.html

